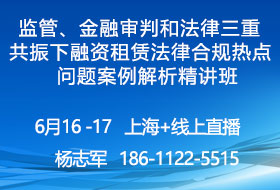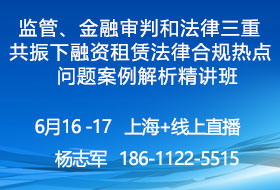制造業轉型緊盯融資租賃
中國目前的實體經濟升級換代,特別是從勞動密集型向資本密集型以及技術密集型的轉型,同樣需要融資租賃產業的金融支持。這也是高層對這個金融行業不斷表示關注的重要原因。
融資租賃,一度被稱為銀行信貸和資本市場之外的“第三大金融工具”。
從2013年開始,李克強總理多次在公開場合和重要會議上提到,融資租賃行業要加快發展,并服務于實體經濟。政府總理多次提到某個特定行業的發展,這并不多見。這種“特殊地位”,是由中國當前實體經濟的現實和這個行業的獨特作用所決定的。
當前,中國實體經濟,特別是民營經濟正從勞動密集型向資本密集型轉型,這是“中國制造”技術升級的必由之路。但一個不可否認的現實是,實體經濟對資本的吸引力并沒有想象的強大,顯然比不上一線城市的樓市。因此,在這個實體經濟的“轉型悖論”之下,融資租賃成了將資金定向“打入”實體經濟,支持其向資本密集階段“晉級”的創新金融工具。
從各國融資租賃產業的發展歷程來看,凡是制造業有過“大轉型”的國家,融資租賃行業都可以得到最充分的發展。當下的中國,融資租賃的市場滲透率僅為發達國家的1/3左右,盡管潛力巨大,但這個產業的發展依然面臨諸多制度障礙。這些“功課”,怎么補?
實體轉型需求
融資租賃誕生于二戰之后,這一時期,美國經濟的最大特點是戰時產能大擴張,而戰后市場卻需求不足,和當下的中國經濟有某些相似性。
此前,大型設備、飛機、船舶的制造商為了擴大銷售,已經普遍采用分期付款模式。但分期付款的問題在于,采購者(工業企業、運輸公司)在付清貨款之前已經取得了標的的所有權,如果采購者發生財務困難或者因其他原因而違約,那么將產生嚴重的信用問題。
于是,廠商開始采取另一種新穎的銷售模式。即在分期付款的基礎上,不轉移標的所有權,即所有權仍屬于廠商,而采購者則獲得使用權,并分期支付標的的租金。當全部租金支付完畢,所有權才歸于采購者,即承租人。
這種將使用權和所有權分離的“分期付款”模式,就是“融資租賃”的雛形。目前,全球的融資租賃業務主要有3種形式,分別是直租、廠商合作和回租,他們都脫胎于這種不轉移所有權的“分期付款”模式。
假設有一家珠三角或者蘇南地區的制造業公司A,根據市場需求或者響應“國家號召”,要對產品進行換代,需要從廠商B手中購買一套價值昂貴的機床,用以制造新產品。但A缺乏資金,而且銀行也不愿意提供這筆貸款。
那么,A可以和租賃公司C合作,由C按照A的要求,出資從B處購買這套機床,然后租給A使用,而A定期繳納租金。在租賃期間,機床的使用權在A,但所有權在C。
以上這種形式一般被稱為直租,另一種常用形式是廠商合作。在直租中,當租期結束,并且C收回投資,機床的所有權才從C轉移給A,此時的A可能還要支付一定的對價。但問題在于,A也可能對于獲得這臺舊機床的所有權并不感興趣,因為產品要經常升級換代,租賃標的也最好不要“砸在手里”。
于是,就產生了廠商合作,即A、B、C三方進行利益捆綁,最后由廠商B負責對舊機床的回購,A不用支付對價取得機床的所有權。換言之,廠商合作即給予了承租人更多的選擇權,有利于其資金的充分利用和技術的不斷升級換代。
另一種租賃形式是回租,即A把企業已有機床賣給B,然后再從B手中租回機床使用。在這種情況下,實際是A從B融資的一種行為,因為,B需要向A支付一筆機床購入的價款。這類似于,B是銀行,而A從B取得了抵押貸款。
經過各國的金融創新,融資租賃的形式已經日益多樣化,并不止于上述3種簡單形式。但從根本上講,融資租賃強調了一種“融資”的本質。
最初,融資租賃的主要目的是廠商,即出租人擴大銷售,但隨著金融創新步伐的加快,其作為融資手段的主要價值更為承租人所看重。對融資租賃的這一優勢,業界稱之為企業將固定資產“盤活”。
一個值得注意的問題是,美國的融資租賃產業發軔于1950年代,勃興于六七十年代。其背景是,在這一時期,美國的實體經濟經歷了一次大轉型,很多實體部門將制造環節轉移到日本、拉美和東南亞,而本土實體經濟實現了從勞動密集型向資本密集型以及技術密集型的轉型。
彼時,美國租賃市場的租賃標的除了常用的飛機、船舶和車輛等交通工具外,主要還包括了計算機通訊、醫療設備等。一定程度上可以說,融資租賃行業的發展對美國IT產業核心硬件研發、精密加工等高附加值環節的崛起,奠定了重要的資金基礎。
因此,在這個意義上講,中國目前的實體經濟升級換代,特別是從勞動密集型向資本密集型以及技術密集型的轉型,同樣需要融資租賃產業的金融支持。這也是高層對這個金融行業不斷表示關注的重要原因。
貨幣“定向配置”
目前,世界各國的融資租賃產業發展程度,幾乎和實體經濟的強弱是一種“正相關”的關系。融資租賃排名靠前的國家都是美國、日本等發達國家,而中國大有后來居上的趨勢。
盡管美國擁有世界上最發達的資本市場體系,實體經濟可以從資本市場籌得長期資金。同時,這個國家也有強大的中小銀行體系,產業部門很容易從銀行籌得短期融資。但事實是,這種強大的金融供給,依然需要融資租賃來進行“不可獲取的補充”。
一項統計數據顯示,早在上世紀90年代末,美國便已有約80%的企業會利用租賃方式取得部分或全部設備,整體租賃滲透率更達30%。所謂租賃滲透率,即一個經濟體租賃交易量占當年企業設備投資總量的比例。可以看出,融資租賃對于美國實體經濟發展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基于中國實體經濟目前的融資現實,中國或許更需要這個行業。一方面,中國資本市場“不發達”—“不發達”并非只體現在融資體量上,更體現在這個市場的“逆向激勵”機制上,少數可以上市融資的公司未必是真正需要資金的“好公司”。
此外,龐大的國有產業部門和地方政府擁有一定程度上的“融資特權”,他們一些不負責任的融資行為,對私營部門特別是中小企業群體的融資產生了強大的“擠出效應”。因此,金融供給根本無法滿足實體經濟特別是廣大中小企業的技術提升和產品升級換代的需求,這無疑是融資租賃行業的機會。
實際上,國家層面早已看到問題所在,這在制造業發展“國家級”綱領文件中早有體現。2015年,國務院印發了《中國制造2025》,部署全面推進實施制造強國戰略,這是我國實施制造強國戰略第一個十年的行動綱領。
在這份文件中,融資租賃被作為一個“重點”來凸顯,文件中5次提到了融資租賃(金融租賃)。一方面,融資租賃首先被定位為“生產性服務業”,并特別強調“生產性服務業”要提高對制造業轉型升級的支撐能力。另外,融資租賃業被定位為針對中小企業轉型升級的重要金融扶持措施。
更值得一提的是,近年來,高層對這個產業的支持態度也非常“高調”。2013年12月,李克強在一家大型金融租賃公司考察時表示,金融租賃產業在我國是“新的高地”,金融租賃產業為實體經濟服務,國家要培育這個產業發展壯大。此后,在李克強總理主持召開的多次國務院常務會議上,融資租賃和金融租賃均多次被提及。
融資租賃這一產業為何上升到國家經濟建設的議事日程?這很大程度和中國當下所面臨的特殊金融“困境”有關。
2014年,我國GDP同比增長7.4%,這個增速是1990年以來的新低。隨后,央行開始通過降息、降準等貨幣政策工具釋放流動性,緩解實體經濟的融資壓力。其中,還數次采取了定向降準政策,比如對支持小微企業或者三農的金融機構,會在存款準備金率上略微下調,旨在“定向”對這些企業釋放資金。
但一個不能否認的問題是,貨幣當局在宏觀層面的意圖是好的,但微觀層面,資金是否真的流到了這些部門,并不能完全被監管部門掌控。政府能“管”銀行,但“管”錢這種事,卻沒有這么容易。因為,任何資金都有逐利的“天性”,它們只會去利潤最高的地方,而不是響應政府的號召。
當房地產部門成為利潤最高的部門,一些資金難免更傾向于貸給開發商或流入炒房者手中。實體經濟下行,一線城市的房價卻節節升高,這種強烈的資金配置反差,背后到底發生了什么?
因此,如果將貨幣的“定向配置”作為一種經濟調控手段,那么融資租賃的“定向效果”更好。因為,它是基于物理設備的融資,企業只有具備了采購設備,并用來擴大生產或改善技術的這個先行條件,才能通過融資租賃“融資”。如果是其他一些融資方式,即便資金真的流入企業,企業也可能轉手“炒錢“,拿去炒樓、炒股或者搞民間放貸。
市場缺陷在哪?
值得注意的是,融資租賃的英文是“Financial Lease”,漢語可翻譯成“融資租賃”,也可以翻譯成“金融租賃”。在國外,兩者就差不多是一個行業,因為承租人的需求都是一樣的,操作的法律手法也大同小異。但在中國,“Financial Lease”卻分化成了“兩個行業”,一個是“融資租賃”,一個是“金融租賃”,國家監管中以兩個行業分立存在,而新聞報道之中卻經常出現混同。
兩者區別很多,但主要在于三點。一是在監管主體上,兩者的區別是前者由商務部監管,后者由銀監會監管。二是資金來源上,前者的資金來源主要是股東的資本金,但后者來源更加廣泛,除了資本金還可以接受股東存款,同時也可以參與銀行間市場的融資。三是監管程度上,后者較前者嚴格,比如后者有信貸規模限制,而前者沒有。
之所以會形成兩個體系,其中包含了一定的“歷史因素”。中國的融資租賃產業始于上世紀80年代,當時正值改革開放初期,國家推動這個產業發展的主要目的是為了引進西方的先進技術和設備。因此,作為金融行業的一個分支,融資租賃行業對外資的開放遠比銀行、證券和保險等行業要早。
因為和引進外資有關,所以我國的融資租賃最早是由外經貿部門監管,而現在仍屬于商務部監管。此外,融資租賃勃興之時,中國銀監會尚未成立。
但后來,融資租賃行業并沒有像當初所設計的那樣,在引進先進技術和設備方面起到足夠作用。因為,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加上中國的高儲蓄率,中國并非一個資本缺乏的國家,需要引進設備的企業并不缺乏資金。相反,由于實體經濟的投資機會的稀缺,以及企業群體普遍的“套利”傾向,中國反倒成為一個資本相對過剩、資產泡沫日益顯現的國家。
因此,融資租賃的發展一直不溫不火,歷經曲折,甚至都少有人關注。轉折發生在2007年。這一年,我國開始試點商業銀行設立金融租賃公司,盡管名字不同,但業務范圍區別并不大。所謂“金融租賃”,仍可歸為廣義的“融資租賃”。
中國的商業銀行是世界上最龐大的“資產管理機構”群體,任何一個金融行業,只要它們“跨界”進入,必然會面臨一次行業發展的“井噴”。在金融租賃開閘之后,一大批銀行系金融租賃公司紛紛成立,由于其巨大的資金優勢,在與融資租賃公司的競爭中越發“后來居上”。
一項統計數據顯示,截至2015年底,我國金融租賃行業總資產大約為1.6萬億元,其中銀行系公司(銀行控股或間接控股)占75%。從增幅上看,行業總規模對比銀行系金融租賃公司全面大啟動的2009年,增加了60多倍。
從統計口徑上看,我國融資租賃和金融租賃行業分成兩大類3種公司:一類是銀監會監管的金融租賃公司,另一類是商務部監管的融資租賃公司,后者又分內資試點融資租賃企業和外資投資融資租賃企業兩類。截止到2015年底,金融租賃企業資產總額約1.6萬億元,內資試點融資租賃企業資產總額約9000億元,外資融資租賃企業約1.1萬億元。
中國的租賃行業潛力巨大,行業的發展也有資金、需求等諸多優勢,但另一方面,“軟環境”卻不甚樂觀。比如,租賃產業的多頭管理便客觀上造成了市場的分割,并不利于行業的健康發展。
顯而易見,金融租賃做著和融資租賃“差不多”的業務,但兩者的資金來源上卻有很大差異,這造成了一種不公平的競爭。與此同時,租賃標的的登記和公示系統也存在分割,這個問題更影響了行業的長遠發展,特別是行業信用的構建。
比如,租賃標的就好比一臺二手車,它的里程、車況等因素是決定其價格的基礎,這個信用記錄要做到客觀真實,重要條件是登記平臺的統一化和標準化。融資租賃也是如此。但目前,我國的標的登記卻有兩個平臺,一是人民銀行的融資租賃登記公示系統,二是商務部的全國融資租賃企業管理信息系統,到底“用誰”、“信誰”?這真是個問題。
一直以來,在對經濟建設的管理中,中國除了地方競爭,還有“部委競爭”。這種智慧用在推動某些行業的高速擴張上,或許有用,但融資租賃是個與實體經濟轉型密切相關的“慢活”、“細活”,統一的監管或許更有價值。
融資租賃,一度被稱為銀行信貸和資本市場之外的“第三大金融工具”。
從2013年開始,李克強總理多次在公開場合和重要會議上提到,融資租賃行業要加快發展,并服務于實體經濟。政府總理多次提到某個特定行業的發展,這并不多見。這種“特殊地位”,是由中國當前實體經濟的現實和這個行業的獨特作用所決定的。
當前,中國實體經濟,特別是民營經濟正從勞動密集型向資本密集型轉型,這是“中國制造”技術升級的必由之路。但一個不可否認的現實是,實體經濟對資本的吸引力并沒有想象的強大,顯然比不上一線城市的樓市。因此,在這個實體經濟的“轉型悖論”之下,融資租賃成了將資金定向“打入”實體經濟,支持其向資本密集階段“晉級”的創新金融工具。
從各國融資租賃產業的發展歷程來看,凡是制造業有過“大轉型”的國家,融資租賃行業都可以得到最充分的發展。當下的中國,融資租賃的市場滲透率僅為發達國家的1/3左右,盡管潛力巨大,但這個產業的發展依然面臨諸多制度障礙。這些“功課”,怎么補?
實體轉型需求
融資租賃誕生于二戰之后,這一時期,美國經濟的最大特點是戰時產能大擴張,而戰后市場卻需求不足,和當下的中國經濟有某些相似性。
此前,大型設備、飛機、船舶的制造商為了擴大銷售,已經普遍采用分期付款模式。但分期付款的問題在于,采購者(工業企業、運輸公司)在付清貨款之前已經取得了標的的所有權,如果采購者發生財務困難或者因其他原因而違約,那么將產生嚴重的信用問題。
于是,廠商開始采取另一種新穎的銷售模式。即在分期付款的基礎上,不轉移標的所有權,即所有權仍屬于廠商,而采購者則獲得使用權,并分期支付標的的租金。當全部租金支付完畢,所有權才歸于采購者,即承租人。
這種將使用權和所有權分離的“分期付款”模式,就是“融資租賃”的雛形。目前,全球的融資租賃業務主要有3種形式,分別是直租、廠商合作和回租,他們都脫胎于這種不轉移所有權的“分期付款”模式。
假設有一家珠三角或者蘇南地區的制造業公司A,根據市場需求或者響應“國家號召”,要對產品進行換代,需要從廠商B手中購買一套價值昂貴的機床,用以制造新產品。但A缺乏資金,而且銀行也不愿意提供這筆貸款。
那么,A可以和租賃公司C合作,由C按照A的要求,出資從B處購買這套機床,然后租給A使用,而A定期繳納租金。在租賃期間,機床的使用權在A,但所有權在C。
以上這種形式一般被稱為直租,另一種常用形式是廠商合作。在直租中,當租期結束,并且C收回投資,機床的所有權才從C轉移給A,此時的A可能還要支付一定的對價。但問題在于,A也可能對于獲得這臺舊機床的所有權并不感興趣,因為產品要經常升級換代,租賃標的也最好不要“砸在手里”。
于是,就產生了廠商合作,即A、B、C三方進行利益捆綁,最后由廠商B負責對舊機床的回購,A不用支付對價取得機床的所有權。換言之,廠商合作即給予了承租人更多的選擇權,有利于其資金的充分利用和技術的不斷升級換代。
另一種租賃形式是回租,即A把企業已有機床賣給B,然后再從B手中租回機床使用。在這種情況下,實際是A從B融資的一種行為,因為,B需要向A支付一筆機床購入的價款。這類似于,B是銀行,而A從B取得了抵押貸款。
經過各國的金融創新,融資租賃的形式已經日益多樣化,并不止于上述3種簡單形式。但從根本上講,融資租賃強調了一種“融資”的本質。
最初,融資租賃的主要目的是廠商,即出租人擴大銷售,但隨著金融創新步伐的加快,其作為融資手段的主要價值更為承租人所看重。對融資租賃的這一優勢,業界稱之為企業將固定資產“盤活”。
一個值得注意的問題是,美國的融資租賃產業發軔于1950年代,勃興于六七十年代。其背景是,在這一時期,美國的實體經濟經歷了一次大轉型,很多實體部門將制造環節轉移到日本、拉美和東南亞,而本土實體經濟實現了從勞動密集型向資本密集型以及技術密集型的轉型。
彼時,美國租賃市場的租賃標的除了常用的飛機、船舶和車輛等交通工具外,主要還包括了計算機通訊、醫療設備等。一定程度上可以說,融資租賃行業的發展對美國IT產業核心硬件研發、精密加工等高附加值環節的崛起,奠定了重要的資金基礎。
因此,在這個意義上講,中國目前的實體經濟升級換代,特別是從勞動密集型向資本密集型以及技術密集型的轉型,同樣需要融資租賃產業的金融支持。這也是高層對這個金融行業不斷表示關注的重要原因。
貨幣“定向配置”
目前,世界各國的融資租賃產業發展程度,幾乎和實體經濟的強弱是一種“正相關”的關系。融資租賃排名靠前的國家都是美國、日本等發達國家,而中國大有后來居上的趨勢。
盡管美國擁有世界上最發達的資本市場體系,實體經濟可以從資本市場籌得長期資金。同時,這個國家也有強大的中小銀行體系,產業部門很容易從銀行籌得短期融資。但事實是,這種強大的金融供給,依然需要融資租賃來進行“不可獲取的補充”。
一項統計數據顯示,早在上世紀90年代末,美國便已有約80%的企業會利用租賃方式取得部分或全部設備,整體租賃滲透率更達30%。所謂租賃滲透率,即一個經濟體租賃交易量占當年企業設備投資總量的比例。可以看出,融資租賃對于美國實體經濟發展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基于中國實體經濟目前的融資現實,中國或許更需要這個行業。一方面,中國資本市場“不發達”—“不發達”并非只體現在融資體量上,更體現在這個市場的“逆向激勵”機制上,少數可以上市融資的公司未必是真正需要資金的“好公司”。
此外,龐大的國有產業部門和地方政府擁有一定程度上的“融資特權”,他們一些不負責任的融資行為,對私營部門特別是中小企業群體的融資產生了強大的“擠出效應”。因此,金融供給根本無法滿足實體經濟特別是廣大中小企業的技術提升和產品升級換代的需求,這無疑是融資租賃行業的機會。
實際上,國家層面早已看到問題所在,這在制造業發展“國家級”綱領文件中早有體現。2015年,國務院印發了《中國制造2025》,部署全面推進實施制造強國戰略,這是我國實施制造強國戰略第一個十年的行動綱領。
在這份文件中,融資租賃被作為一個“重點”來凸顯,文件中5次提到了融資租賃(金融租賃)。一方面,融資租賃首先被定位為“生產性服務業”,并特別強調“生產性服務業”要提高對制造業轉型升級的支撐能力。另外,融資租賃業被定位為針對中小企業轉型升級的重要金融扶持措施。
更值得一提的是,近年來,高層對這個產業的支持態度也非常“高調”。2013年12月,李克強在一家大型金融租賃公司考察時表示,金融租賃產業在我國是“新的高地”,金融租賃產業為實體經濟服務,國家要培育這個產業發展壯大。此后,在李克強總理主持召開的多次國務院常務會議上,融資租賃和金融租賃均多次被提及。
融資租賃這一產業為何上升到國家經濟建設的議事日程?這很大程度和中國當下所面臨的特殊金融“困境”有關。
2014年,我國GDP同比增長7.4%,這個增速是1990年以來的新低。隨后,央行開始通過降息、降準等貨幣政策工具釋放流動性,緩解實體經濟的融資壓力。其中,還數次采取了定向降準政策,比如對支持小微企業或者三農的金融機構,會在存款準備金率上略微下調,旨在“定向”對這些企業釋放資金。
但一個不能否認的問題是,貨幣當局在宏觀層面的意圖是好的,但微觀層面,資金是否真的流到了這些部門,并不能完全被監管部門掌控。政府能“管”銀行,但“管”錢這種事,卻沒有這么容易。因為,任何資金都有逐利的“天性”,它們只會去利潤最高的地方,而不是響應政府的號召。
當房地產部門成為利潤最高的部門,一些資金難免更傾向于貸給開發商或流入炒房者手中。實體經濟下行,一線城市的房價卻節節升高,這種強烈的資金配置反差,背后到底發生了什么?
因此,如果將貨幣的“定向配置”作為一種經濟調控手段,那么融資租賃的“定向效果”更好。因為,它是基于物理設備的融資,企業只有具備了采購設備,并用來擴大生產或改善技術的這個先行條件,才能通過融資租賃“融資”。如果是其他一些融資方式,即便資金真的流入企業,企業也可能轉手“炒錢“,拿去炒樓、炒股或者搞民間放貸。
市場缺陷在哪?
值得注意的是,融資租賃的英文是“Financial Lease”,漢語可翻譯成“融資租賃”,也可以翻譯成“金融租賃”。在國外,兩者就差不多是一個行業,因為承租人的需求都是一樣的,操作的法律手法也大同小異。但在中國,“Financial Lease”卻分化成了“兩個行業”,一個是“融資租賃”,一個是“金融租賃”,國家監管中以兩個行業分立存在,而新聞報道之中卻經常出現混同。
兩者區別很多,但主要在于三點。一是在監管主體上,兩者的區別是前者由商務部監管,后者由銀監會監管。二是資金來源上,前者的資金來源主要是股東的資本金,但后者來源更加廣泛,除了資本金還可以接受股東存款,同時也可以參與銀行間市場的融資。三是監管程度上,后者較前者嚴格,比如后者有信貸規模限制,而前者沒有。
之所以會形成兩個體系,其中包含了一定的“歷史因素”。中國的融資租賃產業始于上世紀80年代,當時正值改革開放初期,國家推動這個產業發展的主要目的是為了引進西方的先進技術和設備。因此,作為金融行業的一個分支,融資租賃行業對外資的開放遠比銀行、證券和保險等行業要早。
因為和引進外資有關,所以我國的融資租賃最早是由外經貿部門監管,而現在仍屬于商務部監管。此外,融資租賃勃興之時,中國銀監會尚未成立。
但后來,融資租賃行業并沒有像當初所設計的那樣,在引進先進技術和設備方面起到足夠作用。因為,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加上中國的高儲蓄率,中國并非一個資本缺乏的國家,需要引進設備的企業并不缺乏資金。相反,由于實體經濟的投資機會的稀缺,以及企業群體普遍的“套利”傾向,中國反倒成為一個資本相對過剩、資產泡沫日益顯現的國家。
因此,融資租賃的發展一直不溫不火,歷經曲折,甚至都少有人關注。轉折發生在2007年。這一年,我國開始試點商業銀行設立金融租賃公司,盡管名字不同,但業務范圍區別并不大。所謂“金融租賃”,仍可歸為廣義的“融資租賃”。
中國的商業銀行是世界上最龐大的“資產管理機構”群體,任何一個金融行業,只要它們“跨界”進入,必然會面臨一次行業發展的“井噴”。在金融租賃開閘之后,一大批銀行系金融租賃公司紛紛成立,由于其巨大的資金優勢,在與融資租賃公司的競爭中越發“后來居上”。
一項統計數據顯示,截至2015年底,我國金融租賃行業總資產大約為1.6萬億元,其中銀行系公司(銀行控股或間接控股)占75%。從增幅上看,行業總規模對比銀行系金融租賃公司全面大啟動的2009年,增加了60多倍。
從統計口徑上看,我國融資租賃和金融租賃行業分成兩大類3種公司:一類是銀監會監管的金融租賃公司,另一類是商務部監管的融資租賃公司,后者又分內資試點融資租賃企業和外資投資融資租賃企業兩類。截止到2015年底,金融租賃企業資產總額約1.6萬億元,內資試點融資租賃企業資產總額約9000億元,外資融資租賃企業約1.1萬億元。
中國的租賃行業潛力巨大,行業的發展也有資金、需求等諸多優勢,但另一方面,“軟環境”卻不甚樂觀。比如,租賃產業的多頭管理便客觀上造成了市場的分割,并不利于行業的健康發展。
顯而易見,金融租賃做著和融資租賃“差不多”的業務,但兩者的資金來源上卻有很大差異,這造成了一種不公平的競爭。與此同時,租賃標的的登記和公示系統也存在分割,這個問題更影響了行業的長遠發展,特別是行業信用的構建。
比如,租賃標的就好比一臺二手車,它的里程、車況等因素是決定其價格的基礎,這個信用記錄要做到客觀真實,重要條件是登記平臺的統一化和標準化。融資租賃也是如此。但目前,我國的標的登記卻有兩個平臺,一是人民銀行的融資租賃登記公示系統,二是商務部的全國融資租賃企業管理信息系統,到底“用誰”、“信誰”?這真是個問題。
一直以來,在對經濟建設的管理中,中國除了地方競爭,還有“部委競爭”。這種智慧用在推動某些行業的高速擴張上,或許有用,但融資租賃是個與實體經濟轉型密切相關的“慢活”、“細活”,統一的監管或許更有價值。
| 培訓公告 | ||
| 9月23-24日 | 蘇州-南亞賓館 | 融資租賃資產管理、風險防控與法律實務操作高級培訓班 |
| 歡迎垂詢 133-3106-9587 楊志軍 | ||
| 或登陸http://www.tl17.net了解課程詳情。 | ||
上一篇:實務:融資租賃保理的基本要素
下一篇:聽聽這家租賃公司老總談汽車融資租賃發展的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