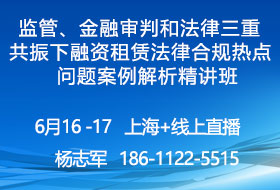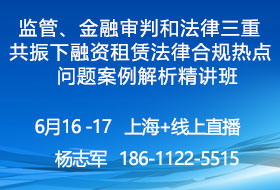中國金融租賃公司:面對“資源詛咒”
在世界各國經濟發展的進程中,有一個很獨特而普遍的現象,即一個國家的自然資源稟賦越優越,其后續發展的勁道和質量反而會越低下,這種狀況被稱作“資源詛咒”。在中國的融資租賃行業中,有這樣的一個企業群體,他們口含“金鑰匙”出生,擁有超越群倫的體制資源、資金資源、市場資源,甚至政治資源,在這些優越初始資源稟賦的支撐下,短短數年之內,他們發展迅猛,雖然只有極低的行業企業數量占比,但是卻實現了近半的行業資產規模——他們就是中國金融租賃公司群體。
但是,最近的情況似乎有了一些新變化,一些似乎可以被視為“資源詛咒”征兆的新變化。
一、其興也勃焉
八年前,當中國金融租賃公司在次貸危機爆發的大背景下,被中國政府“重啟”的時候,其他的融資租賃公司群體的內心中,不時泛起的,是“狼來了”的緊張與不安。但是,很快這些融資租賃公司就發現,自己的擔心,至少階段性地,純屬多余——因為金融租賃公司并沒有“入侵”到,自己以中小型民營企業為主體的市場空間,而是在身邊呼嘯而過,直接打入了原本屬于銀行對公信貸業務中,一部分自己幾乎從未涉足的“高端”客戶群體市場。
八年后,檢索金融租賃公司當年的如此舉動,我們可以清晰而簡潔地表述個中因由:實現優勢資源支撐下的“監管套利”。在需求端,銀行業務的監管規則存在,導致相當數量企業的資金需求,無法在銀行體系內得到有效滿足:其一是因信貸政策規制投放方向而產生的資金需求——比如來自于房地產和高能耗企業的資金需求;其二是因信貸政策限定投放額度,或者因信貸條件無法達成而產生的資金需求——比如對于單一企業的最高授信額度限制,以及雖然未超授信額度,但因不具備銀行要求的保證條件而無法“提款”等原因,所壓抑的資金需求;其三是因銀行經營的“屬地化”政策區隔所導致的異地實體企業,無法獲得本地銀行優勢價格資金的需求。在供給端,從銀行體系的角度,金融租賃的出現,令其獲取了一個有效的監管回避工具:可以利用“租賃通道”機動選擇投放方向,也可以通過“金融租賃”實現對特定客戶企業在“弱化”保證條件的同時,達成“增信”的效果,以及利用“金融租賃”的全國經營資質,實現實際意義上跨地域經營。而在供需對接的交易環節,當時依舊保持的高速經濟增長經濟背景,房地產市場在次貸危機后的報復性價格上漲,國有高能耗企業的體制身份,以及地方政府在GDP考核導向下所愿意提供的隱含信用背書,都成為銀行堅定“引爆”這些為監管所抑制市場需求的充分理由。
這種在銀行體系的資金資源優勢、市場資源優勢支撐下,利用商業銀行和金融租賃兩個不同領域監管差異的套利行動,是造成中國金融租賃快速發展的最核心推動力量,換一個通俗的說法,就是在規避監管的動機下,銀行體系通過從母公司銀行信貸資產到子公司金融租賃資產的“乾坤大挪移”,“造就”了中國金融租賃早期快速啟動,以及稍后“逆勢”強力發展的金粉表象。
雖然,在中國金融租賃公司隨后的發展過程中,投放方向上增添了過剩產能“僵尸企業”和地方政府融資平臺這樣的“新面孔”,許多融資租賃企業也“典身”成為銀行資金的“通道”,“租賃通道”也開辟出新的跨境資金通道功能,以及,借助金融租賃資產交易來“調整”銀行報表以操控某些外部監管指標的手法也訴諸使用,但是,這最為核心的“監管套利”主體邏輯卻沒有發生根本變化。也正是因為這個最根本的邏輯依然在運行,我們才不但能夠清楚地明了,金融租賃公司業務在相當一段時間內來自母公司銀行分支行推薦,金融租賃公司主要做“大客戶和大項目”的經營定位,諸多金融租賃公司開業之初或數月之內資產規模即達百億數量級等等這些周知現象的真正底因,而且,我們還能由此洞悉,近期演繹愈發熾烈的金融租賃同質化競爭狀態(參閱“李喆融資租賃工作室”[微信公號:huaibang2015]行業述評文章:《重壓下的突圍:2016中國融資租賃之夏“祭”》),金融租賃公司與過剩產能企業交易中不斷走低的租賃利率,金融租賃公司與融資租賃公司建立起實質為“經紀”合作的戰略合作關系等等行業現象背后所暗示的,因自身可控的“監管套利”市場資源快速趨于耗盡,所引發的為繼續保持“監管套利”收益不至快速下降,而付出種種努力和博弈的根由所在(參閱:“李喆融資租賃工作室”[微信公號:huaibang2015]行業述評文章:《租賃大佬們的“三十六計”:融資租賃資產“食物鏈”上的計謀勾畫》)。
但是,新的情況變化是,除了這個主體邏輯所內生導致的,金融租賃公司自身可控市場資源在快速耗盡之外,外部的形勢也正在發生變化,而對于金融租賃公司而言,這些外部形勢的變化,也許要比市場資源的消耗更加致命,因為,其所沖擊的,正是“監管套利”邏輯得以成立的所有基礎性條件。
二、履霜堅冰至
次貸危機爆發后,“宏觀審慎監管”成為在各個時事財經媒體上出現的一個高頻詞匯。“宏觀審慎監管”的目的,就是為了消除從前在金融分業或混業“微觀審慎監管”框架下,導致的所謂“合成謬誤”——大量金融企業在微觀監管層面的合規經營動作,其效應合并后,反而會形成更可怕的宏觀系統風險。這種合成謬誤所導致的宏觀系統風險,并非遠在美國或將發于未來,實際上,中國2015年夏天的“股市巨震”,就是一個現實而令人震撼的,近在咫尺真實案例。中國金融的監管結構和監管效度,在中央政府“不發生系統性區域性風險”底線要求的指示之下,必然要發生質的變化和飛越,近期關于改革“一行三會”監管架構所展開的“單一央行模式”與“一委、一行、一會、一局”爭論,不過是這種監管質變將要發生的最初征兆而已。而在“宏觀審慎監管”框架在完整建立起來之前,原有的“微觀審慎監管”層面上所展現出的,則是全面趨緊的動向——信托、基金子公司、互聯網金融領域等一系列的資產“穿透”要求、嚴禁“資金池”等監管動作頻出,近日保監會高層官員對保險企業不可成為大股東“融資平臺”的發言,措辭嚴厲而盡展威懾,融資租賃公司則被暫拒新三板,凡此種種,俯拾皆是。所以,對于金融租賃公司一貫賴以發展的“監管套利”經營邏輯而言,外部總體上監管環境的趨勢性變化,正在形成對其釜底抽薪的一記重擊。
在需求端,金融租賃公司“監管套利”邏輯框架下的市場需求,無論就其需求本身的“有效性”還是此類需求所可獲得的外部信用背書支持效度,都出現了惡化的跡象。所謂需求的“有效性”,是指需求本身所具備的信用債務自償能力,也即企業風險分析工作中通常所指的“第一還款來源”的可靠性。根據十八屆三中全會《公報》中,“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的最新提法,對“市場”的倚重,已然發生了從“基礎性”到“決定性”顯著提升。而市場發揮“決定性”資源配置作用的一個重要表現,就是“市場退出”——這就是“去產能”和淘汰僵尸企業等等治理動作背后的政策根由所在。然而,這種“退出”一旦啟動,對于金融租賃公司的“監管套利”邏輯而言,不但意味著套利市場空間在需求端的萎縮,同時,還意味著“退出”過程必將伴生著痛苦的租賃資產質量惡化狀況出現。近期,我們在云維股份的債務危機中,看到了招銀租賃的身影,而興業租賃也在聲動一時的東北特鋼信用違約案件中,發起訴訟。這些因大型國企違約導致的金融租賃資產出險,似乎,并不能完全用“偶然”來做解釋——已經有人指出了招銀租賃近兩年租賃資產規模增長乏力的現象,而近年一貫以“綠色金融”作為經營指向的興業租賃,面向東北特鋼實施投放的舉動,也鑿然值得品味。當然,在“監管套利”邏輯下,需求端出現經營風險并不是一件意外的事情,真正意外的,是期望中的“隱性擔保”并未如期出現——東北特鋼違約案件中遼寧省政府“逃廢債”的態度,給各方債權人內心帶來了極大震動。雖然,我們依然可以看到云南省政府和山西省政府在云維股份債務危機和七大煤企融資安排方面的積極行動,但是,一個不可否認的事實卻是,地方政府的信用背書效力,正在顯示出弱化的征兆——從前彼此默契的心理契約已然破裂,地方政府現在需要用非常高調主動的具體行動,才能建立起金融機構在類似“債務重組”事項上的謹慎信任,并且,這“謹慎信任”當中,包含了多少無可奈何的意味,也只能由這些債權人自己,去獨自體會了。總之,金融租賃“監管套利”邏輯在需求端的市場空間,以及交易環節的信用背書這兩個方面所倚重建立的基礎,正在出現瓦解的跡象。
在供給端,金融租賃公司群體除了正在遭受來自于內部競爭加劇所導致的,“監管套利”邏輯下“利差空間”的不斷壓縮以外,其過往獨有的資金資源優勢,也在因外部資本市場的發展,而受到侵蝕。從中國金融改革的方向看,降低銀行體系的“間接融資”比例,發展資本市場,提升資本市場“直接融資”比例,是一項重要的任務。換言之,中國金融市場的金融“脫媒”程度,將在政府政策的推動下,呈現出一種加速態勢。有統計數據顯示,2016上半年,以租賃資產作為基礎資產的ABS規模,已經達到500億。也許,這區區500億與行業近5萬億的資產規模相比,還顯得微不足道,但是,如果將之與2016年上半年全行業2400億的資產增量相對比的話,我們就可從另一個角度發現,資本市場融資與融資租賃行業新增資產形成之間的“相關度”,已經超出了許多人的想象。與資本市場融資規模不斷擴大同步出現的,是租賃資產ABS的價格在持續走低。近日平安租賃發行25.62億的ABS,利率為3.59%——大幅低于“1-5年”的貸款基準利率4.75%,由此我們可以發現,如果說目前的互聯網金融,其發展僅僅可能在“量”的方面對傳統銀行體系發起有限沖擊的話,那么,ABS資本市場融資產品已經可以在“價”的方面,對傳統銀行的資金供給,產生現實的替代效應。但是,對金融租賃公司資金資源優勢的沖擊,還遠遠不止來自國內——2016年8月,華科融資租賃以5.20%的票面價格,在新加坡成功發行為期3年的5億元的人民幣境外債券——有理由相信,出于加速人民幣國際化的內在需要,此類跨境人民幣資本市場產品,因其可以刺激人民幣的在岸或離岸市場廣度及深度擴展,將會不斷得到政策支持和市場呼應。此外,金融租賃公司雖然在貨幣市場依然保持一定優勢,并且,2016年8月頒行的《全國銀行間同業拆借市場業務操作細則》也進一步提升了金融租賃公司在貨幣市場交易的操作效率,但是貨幣市場拆入資金所形成的短期負債,與金融租賃公司動輒三至五年的長期資產之間,內在的期限錯配,無法得到有效協調。所以,貨幣市場的優勢僅可以為金融租賃公司在流動性和資金頭寸管理方面,提供便利,而對于在負債端的絕對競爭優勢的保持和建立,助益有限。
山雨欲來,風云變色之勢,似已初顯。然而,另外存在的一些形勢力量,其所產生的“對沖”效果,還是讓局勢的演變,平添幾許變數:宏觀審慎監管框架還遠未成熟,而微觀層面監管與監管規避的多重博弈,也會令許多監管手段效用大減;在去產能進程中的政策態度,相對于“產能消滅”而言,“產能消化”才是真正的理智首選,而新常態下的中國經濟增長,也不可能放棄政府投資的拉動作用;金融租賃公司群體也一樣會充分利用中國資本市場的發展,來進一步來保持和強化自身在資金資源方面的傳統優勢。
但是,所有的跡象至少可以表明,中國金融租賃公司賴以快速發展的“監管套利”經營模式,正在逐步走入窮途——在中國金融租賃公司依靠其獨特的資源稟賦,實現耀眼升騰之后,其現在所要面對的,卻是同樣因這些稟賦優勢而招致的“資源詛咒”。
【“李喆融資租賃工作室”行業述評文章】
| 培訓公告 | ||
| 9月23-24日 | 蘇州—江南四季酒店 | 融資租賃資產管理、風險防控與法律實務操作高級培訓班 |
| 歡迎垂詢 133-3106-9587 楊志軍 | ||
| 或登陸http://www.tl17.net了解課程詳情。 | ||
上一篇:全面“營改增”對融資租賃業務中各主要交易方的影響
下一篇:融資租賃如何開展盡職調查?(僅供參考)